刑法论文:外部和地区大国的消极反恐政策与“越反越恐”现象
来源:985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0-01-05 1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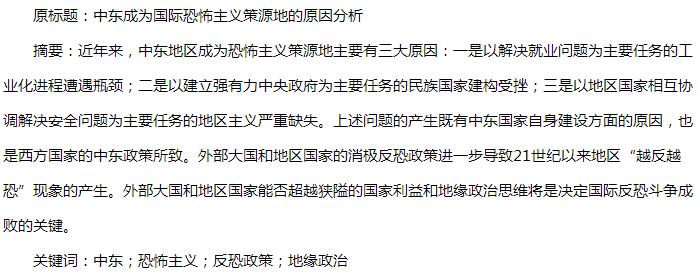
在关于中东恐怖主义的研究中,西方学术界倾向于从宗教视角探寻该地区恐怖主义的根源。尽管这种研究范式在西方学界非常流行,但由于它反映的是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教固有的误解和偏见,因此缺乏全面性。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诞生于中东地区的一神教,具有一些相似性。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曾是长期往来于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商人,该地区广为流传的故事因而成为伊斯兰教教义的重要来源。②“如同其他宗教一样,伊斯兰教崇尚和平、关爱生命。”③在中东地区,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形成均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源。因此,本文的研究将侧重于宗教极端主义受众群体的成因。近年来,中东、非洲乃至欧美国家大量青年成为宗教极端思想的追随者,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本文认为,上述现象的原因有着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根源,突出表现为地区国家工业化、民族国家建构以及地区主义的失败。阿拉伯国家的自身建设问题,以及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中东政策都是造成此类现象的重要原因所在。同时,西方大国和地区国家将反恐问题工具化则是造成“9·11”事件以后中东“越反越恐”现象的主要原因。
一、中东地区宗教极端主义蔓延的原因
宗教极端主义是当今中东恐怖主义的主要思想根源,中东地区宗教极端主义的形成和扩散既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也有着国家治理和地区治理失败等方面的原因。
(一)工业化失败是少数阿拉伯国家青年成为宗教极端主义思潮追随者的经济和社会根源。
尽管人类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但工业化作为现代国家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并未削弱。工业化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既是现代国家保障就业的重要手段,也是其他产业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由于普遍没有实现工业化,阿拉伯国家的第三产业发展也严重滞后于世界其他地区。此外,工业化也是培育具有理性主义精神的中产阶层的必要条件。
根据收入水平,阿拉伯世界可以简单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高收入的海湾阿拉伯产油国,另一类是其他低收入的阿拉伯国家。尽管收入水平不同,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湾阿拉伯产油国依靠丰富的石油资源开采一夜暴富,迅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然而,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工业化的提升或完成,也不意味着充分就业和社会的整体发展。部分阿拉伯产油国虽然建立了石化工业,利用石油财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但真正从事这些行业的并非本国就业人口,而是外来劳工。相反,大量本国青年却坐拥财富而无需就业。这可以从海湾阿拉伯国家外来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中看出,如卡塔尔的外来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4.91%,而阿联酋的外来人口更是高达88.5%,即使是本国人口较多的沙特,外来人口比例也占32.99%(见表1)。

其他阿拉伯国家则大多因为国家财政极为贫弱,不仅从未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产业结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些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被日益边缘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弃儿”.埃及等阿拉伯国家虽然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并未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当前,农业和畜牧业仍然是相当一部分阿拉伯国家经济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
由于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阿拉伯国家的就业形势,特别是青年就业形势一直非常严峻。联合国发展署出版的《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揭示了阿拉伯国家面临的严峻现实。据2009年《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统计,2005年阿拉伯国家约有20.3%的人口生活在每天不足两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之下,其中,埃及低于国际贫困线标准之下的人口比例为41%,也门低于国际贫困线标准之下的人口比例为59.5%.2005年,阿拉伯国家平均失业率为14.4%,其中毛里塔尼亚失业率为22%,而当年全球平均失业率为6.3%.①同样,美国和平基金会发布的“2015年脆弱国家指数”根据人口压力、难民和流离失所群体、不平衡发展、贫困和经济衰退、国家合法性、公共服务、人权、安全设施、外部干预等指标,对全球178个国家进行了统计,索马里(第二)、苏丹(第四)、也门(第七)、叙利亚(第九)四个阿拉伯国家进入全球十大脆弱国家的行列。②青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当政府缺乏为青年群体提供就业保障的能力而导致其无法工作时,他们便会寻求其他“实现自我”的途径,其中不乏走向街头进行示威抗议,或者接受极端宗教意识形态的蛊惑走上战场的人。2011年发端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此后演变成一场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示威抗议浪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量青年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对政府抱有不满情绪。突尼斯青年布瓦吉吉自焚事件充分显示了青年失业可能对政权稳定所造成的巨大冲击。除了活跃于街头的青年群体外,有的青年则追随极端组织,并最终走上战场。
青年群体不仅是“基地”组织的中坚力量,也是“伊斯兰国”组织重要的招募对象。2001年“9·11”事件的21名肇事“基地”组织成员中,有17名是来自沙特的青年。①有数据显示,“伊斯兰国”组织外籍战斗人员数量已逾万人,有些来自失业率较高的贫穷阿拉伯国家,如突尼斯(约6,000人)、约旦(约2,000人)等,有些则来自富裕海湾阿拉伯产油国,如沙特(2,500人)等。②
(二)民族国家建构的失败为恐怖主义滋生创造了条件。
以民族国家认同为核心的国家结构以及民族国家体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却伴随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成为当代国际体系的基础。伊斯兰教的宗教共同体观念、真主主权观念以及“圣战”观念是伊斯兰国际体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西方的民族国家体系观念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并成为伊斯兰世界与国际体系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一。③然而,民族国家体系无论合理与否,却已经成为当代国际体系的重要基础,并成为国内治理的外部结构。主动适应则是伊斯兰世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民族国家建构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意义主要在于中央政府权威的确立和得到认可。④“没有政府,就没有国家。”⑤诚然,阿拉伯国家已经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共和制国家不仅有总统、总理以及内阁部长等职位,还有议会和司法机关,君主制国家除了王室以外,还设立了各种具有立法和司法职能的委员会。⑥然而,现代民族国家的结构形式并不能掩盖阿拉伯国家政治社会的传统性。阿拉伯世界大体上仍然是一个由宗教和部落组成的社会,对宗教和部落的认同远高于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不仅如此,宗教的不同派系,以及部落内部不同势力的划分,成为现代阿拉伯世界民族国家建构不得不面临的严峻挑战。
宗教、教派、部落、族群矛盾深刻影响着中东的民族国家建构。例如,黎巴嫩的基督教马龙派、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分别掌握总统、总理和议长三大政治核心职位,该国虽然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但其境内什叶派力量黎巴嫩真主党对伊朗唯命是从,对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的教派认同甚至超越对中央政府权威的认同。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则由什叶派担任总理,库尔德人担任总统,逊尼派出任议长,但掌握实权的什叶派在外交上也唯伊朗马首是瞻,库尔德人更热衷于维护其自治权,逊尼派则积极寻求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逊尼派的政治支持,这导致伊拉克政治呈现出明显的分裂和分化特征。利比亚则是由部落组成的社会,卡扎菲时期,国家政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个部落集团对另一个部落集团的统治;利比亚内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部落集团对另一个部落集团的战争。①
因此,对各自宗教和部落认同的强化客观上增加了阿拉伯世界民族国家建构的难度,直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并最终导致国家有效治理的缺位。混乱和失序是中央政府权威得不到认同和认可的合乎逻辑的后果,国家治理的缺位为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了空间。黎巴嫩、伊拉克、也门、索马里以及利比亚是上述情况的极端体现,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但程度不一。
当然,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和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等部分阿拉伯国家推行的威权统治,在客观上压制了青年群体以及社会各阶层合理的政治表达,助长了他们对中央政府权威的不满,并最终导致中央政府权威的弱化。
(三)地区主义的失败为恐怖主义势力的生存和壮大提供了条件。
地区主义不仅包括地区经济一体化,还包括地区内国家特别是地区大国之间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内的政策协调。二战后,欧洲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在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东亚的崛起也在一定意义上得益于地区国家之间的频繁互动以及在重大分歧上保持克制的态度。
中东地区因其宗教、民族和部落矛盾以及不同族群跨境而居等复杂的现实情况,本就需要国家之间相互协调,尤其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然而,由于中东地区不存在一个能够涵盖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以及以色列的地区安全框架和地区组织,因此建立中东地区集体安全机制至今遥遥无期。成立于1945年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是世界上最早的区域组织之一,但因内部分裂未能在安全问题上发挥有效作用。海湾合作委员会成立的目的主要是防止1979年后伊朗对外输出“革命”,曾在安全问题上发挥过一定作用。然而,海合会于2011年卷入巴林危机以及2015年强力介入也门乱局,表明该组织更像是军事集团或者诸多冲突的一方,而不是协调海湾地区内各方安全利益的包容性机制或组织。
地区主义的缺位无疑为“伊斯兰国”组织的发展壮大以及政治实体化创造了条件。“伊斯兰国”组织存在于内陆地区,如果其武器供应系统、对外传播的互联网系统、石油走私系统以及对外贸易系统被切断,其向外拓展的势头将得到有效遏制。“伊斯兰国”组织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区大国间缺乏有效措施遏制其发展的安全合作机制。
二、西方国家的政策与中东恐怖主义
工业化、国家建构和地区主义的失败固然有阿拉伯国家自身文化传统、地理环境和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但美欧等西方国家作为数百年来对中东地区有着重要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的外部力量,其推行的中东政策也是造成中东宗教极端主义蔓延的重要原因。
第一,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强势竞争和利己政策是导致阿拉伯世界工业化发展滞后的重要外部原因。自然条件是制约阿拉伯世界工业化的重要内因之一。除海湾地区盛产石油以外,其他阿拉伯国家基本上属于资源匮乏型国家。阿拉伯世界虽地域广袤,但大多为沙漠地带,不仅严重缺乏现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水资源,而且人口密度不够,劳动力资源不够集中。这些因素客观上制约了阿拉伯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但欧洲国家长期殖民中东的历史遗产和利己的经济政策构成了阿拉伯国家工业化落后的重要外部原因。阿拉伯世界与欧洲国家隔地中海相望,但无论是在政治安全方面,还是经济方面,地中海都没有成为能够保护阿拉伯世界的屏障。相反,欧洲国家正是通过地中海进入中东地区,并得以一度长期殖民阿拉伯国家的。在经济上,欧洲地区的商品通过地中海不断销往阿拉伯国家。在此背景下,阿拉伯国家不仅丧失了工业化的动力,而且丧失了基本的竞争力。不仅如此,欧洲国家的竞争也是阿拉伯国家产品未能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原因。北非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地中海沿岸国家地质和气候条件类似,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橄榄油远销世界各地,而突尼斯等北非国家的橄榄油则滞销国内,这显然和欧洲国家的强势竞争有关。
20世纪90年代,欧洲国家倡议的“欧洲-地中海伙伴计划”(又称“巴塞罗那进程”)表面上承诺建立一个“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地区,但实则是欧洲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实现自身利益,重新将地中海沿岸国家纳入由其主导的跨地中海地区经济体系的战略措施。尽管地中海沿岸国家对欧盟的出口有所增加,但并没有在工业化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方面为上述国家带来实质利益。在贸易结构方面,地中海国家出口到欧盟的货物主要是能源和初级产品,而非工业品。地中海国家不仅受损于欧盟保护主义的农业政策,还受害于欧盟强加给纺织业的严格限制。①
第二,西方国家的干预破坏了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对于任何非西方社会来说,构建一个以强有力中央政府为核心的民族国家结构都具有相当的难度,阿拉伯国家也不例外,因为民族国家本身是产生于并适应西方文化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对于阿拉伯世界民族国家建构而言,外部力量本应采取宽容和支持的立场。然而,西方国家非但没有在阿拉伯世界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采取支持立场,反而多次以推动中东国家民主化等不同理由进行军事干预甚至发动战争,即使是出于善意,也在客观上破坏了阿拉伯世界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
2011年,西方国家滥用联合国关于设立禁飞区的授权发动了利比亚战争,既推翻了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也摧毁了该国脆弱的民族国家结构。对此,基辛格指出,“利比亚地广人稀,彼此争斗的不同教派和部落除了曾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外,没有共同历史。推翻暴戾的独裁者卡扎菲产生的实际结果,是抹掉了带有国家统治色彩的所有痕迹”②。
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对内具有独裁的各种特征,包括残酷镇压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的反政府力量,对外则表现出挑战国际体系规则的倾向,如先后对伊朗和科威特发动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但不能否认,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通过威权统治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并利用这种权威制约了国内矛盾的发展。同时,该时期伊拉克作为民族国家的认同和意识也基本确立起来,突出表现为两伊战争期间大量伊拉克什叶派力量超越宗教认同而追随萨达姆政权进攻伊朗。然而,美国先是以反恐反核扩散,后以反独裁等十分牵强的理由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仅推翻了萨达姆政权,而且摧毁了伊拉克本已十分脆弱的民族国家结构,并直接导致战后伊拉克局势长期混乱。
叙利亚也是由不同民族和教派构成的国家,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来自占全国人口不足10%的阿拉维派,该派是什叶派的分支,其余人口大多为逊尼派和基督徒。尽管阿萨德政权的建立是否合乎民主程序一直饱受争议,但该政权事实上主要依靠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进行超越教派的统治,具有民族国家结构的特点。①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西方国家以推广民主为由支持叙利亚反对派,致力于推翻阿萨德政权,不仅威胁到政权稳定,而且威胁到叙利亚本已非常脆弱的民族国家结构。
第三,西方国家的平衡和分化政策是造成中东地区分裂的重要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英法两个大国之间达成《赛克斯-皮科协定》,划定各自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构成此后中东地区分裂版图的原型。不仅如此,西方因素也贯穿了中东地区分裂进程的每一个阶段,并使得该地区的分裂态势不断加深。②
冷战结束后,以海湾战争为分水岭,中东地区逐步形成了由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为实现对中东地区的掌控,美国将该地区的力量划分为两类,一是亲美温和力量,包括海湾国家、约旦、摩洛哥、突尼斯、埃及以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等;二是反美“激进”力量,包括伊朗、利比亚、叙利亚、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这种划分意在鼓励和支持亲美温和力量对抗反美“激进”力量,不仅加剧了地区国家间的对抗,而且加剧了地区分裂的态势。中东地区国家之所以难以在反恐等重大地区问题上保持协调,很大程度上与美国人为制造的矛盾和利益分歧密切相关。
三、外部和地区大国的消极反恐政策与“越反越恐”现象
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开启了全球性反恐运动。然而15年来,国际恐怖主义非但没有被根除,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阿富汗塔利班势力历经多年围剿,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伊拉克的“基地”组织分支最终发展壮大,演变为席卷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广大地区的“伊斯兰国”组织,并且在世界各地到处煽风点火。这凸显了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越反越恐”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包括恐怖主义自身的顽固性,但同时也是外部和地区大国没有采取适应反恐形势需要的政策所致。
第一,美国等国的消极反恐政策非但不能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反而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重要原因。尽管人们无须质疑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所包含的真实反恐意图,因为“9·11”事件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安全冲击为美国的反恐战争提供了强大动力,但此后15年间,美国在中东地区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是否真正出于反恐目的,仍存在诸多疑点。换言之,美国也许抱持了一种反恐的“善意”,但它更多则是将反恐作为一种名义或者是一种次要目标,以服务于其他目标。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之一是正在寻求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萨达姆政权与“基地”组织有牵连。但直至战争结束,美国仍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萨达姆政权支持“基地”组织,也没有找到萨达姆政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真实目的意在按照美国的政治模式对伊拉克进行民主化改造,并试图以此作为其中东地区民主化改造的样板。尽管美国试图自圆其说,将民主化解读为根除恐怖主义的手段,但这反而暴露了美国在中东地区推广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意图。①事实表明,美国以反恐名义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非但没有根除恐怖主义,反而使得伊拉克成为恐怖主义势力新的策源地。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解散了伊拉克安全部队,致使伊拉克陷入了安全真空,为恐怖主义势力在该国的发展和壮大创造了条件。
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的调整可以解读为“待在必须待在的地方,能撤离时就撤离(engage where we must,disengage when wecan)”,②这一政策调整从反面表明,美国并不是真正致力于国际反恐大义的国家。如同推翻萨达姆政权并解散其安全部队造成了伊拉克安全真空一样,奥巴马撤军伊拉克也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由于秩序失控,伊拉克成为“基地”组织赖以扩大影响的另一重要战略据点。在此情况下,美国本应加大反恐力度,然而奥巴马政府非但没有投入更多的战略资源,反而在伊拉克安全部队并不具备反恐能力的情况下草率做出了从伊拉克撤军的决定,致使伊拉克安全形势每况愈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乘机坐大。
同样,当“伊斯兰国”组织于2014年初迅猛扩张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后,美国迫于压力不得不加大其在中东地区的反恐力度。美国所采取的行动固然具有反恐的一面,但其他意图也同样存在,甚至希望借助“伊斯兰国”组织力量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目标。比如,美国为“叙利亚自由军”提供的武器落入了“伊斯兰国”组织之手,美国也没有在其完全有能力的情况下摧毁“伊斯兰国”组织走私石油的通道。③在俄罗斯于2015年9月开始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后,美国和法国也加大了对中东地区军事投入的力度。就其时机选择而言,此举与其说是反恐,不如说是为了与俄罗斯争夺中东问题的话语权和地缘政治影响力。
总而言之,在2001~2015年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虽然一直高举反恐大旗,但并没有采取积极的反恐战略,而是将反恐问题作为推行中东政策的工具。美国以反恐名义发动的战争非但没有达到消灭恐怖主义的目的,反而制造了恐怖主义赖以滋生所需要的土壤。奥巴马政府“躲避”和“利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政策更为该组织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第二,外部大国的军事干预既没有达到治标的目的,也不可能完成治本的任务。诚然,军事手段在反恐方面的确取得过一些积极的成效,特别是在外部大国空中打击和当地地面武装相互配合的情况下,反恐战争能够取得势如破竹的效果。如2001年美国推翻塔利班政权,以及2015年第四季度俄罗斯和美国相继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加大力度,取得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收复失地战役的重要胜利等。这些外部军事干预确实摧毁了“伊斯兰国”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控制的基础设施,如石油走私的运输系统等,而且能够摧毁它们的有生力量。
在当前恐怖主义势力“准国家化”的背景下,外部大国的军事打击也许是一种无法回避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外部大国的军事干预是一种必然有效的解决办法。即使外部大国没有对反恐问题采取工具化的立场,真正致力于反恐战争,其军事干预的手段也无法达到消灭恐怖主义势力的目的。军事干预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国家崇尚实力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真正有效的反恐治本手段。
过于依赖外部大国军事干预解决反恐问题的错误在于将该模式在传统安全领域内的成功经验应用于非传统安全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海湾战争为标志,外部大国的军事干预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是上述军事行动涉及的是传统安全领域,其对象是特定国家的成建制军队。而如今活跃在中东地区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势力是植根于该地区脆弱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并拥有极端意识形态体系的恐怖组织,外部大国的军事干预即使能够部分摧毁其有形力量,也断然难以破坏其组织机制和网络,①因为军事打击无法根除无形的且基于特定经济基础的思想意识。
美国虽然在2001年摧毁了为“基地”组织提供庇护的塔利班政权及其基础设施,但并没有消灭恐怖主义,反而使得阿富汗成为向中东以及其他地区源源不断输送恐怖主义力量和意识形态的策源地之一。2003年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在伊拉克所实施的军事行动有反恐的一面,但终究也未能剿灭恐怖主义势力。同样,即使美国等外部大国能够摧毁“伊斯兰国”组织的部分有生力量以及基础设施,也断然难以从根本上防止恐怖主义滋生。
此外,外部大国的军事干预也更容易被极端主义势力解读为外部入侵,或者是西方势力对伊斯兰世界的欺辱,并成为恐怖主义势力借以招募新成员的口号。无论是对于中东本土的年轻人,还是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被边缘化的穆斯林群体来说,反对西方入侵都是极具煽动性的口号。哈佛大学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Walt)认为,“伊斯兰国”组织已经演变为一个“革命性国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外部力量推翻一个革命性的国家往往会加强强硬派的力量,助其扩大影响,起到相反的作用。①
第三,部分地区内国家的消极态度是“越反越恐”现象的另一深层根源。中东地区恐怖主义滋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地区主义的缺位。“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标志着恐怖主义势力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组织,而是已经演变为谋求控制一定规模的领土和人口,并按照其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对其进行统治的政治实体。但如前文指出,其生存依赖于一系列后勤保障和供应系统,包括武器走私系统、石油走私系统、金融系统、对外传播的互联网系统以及人员招募系统等,若能切断上述任何一个系统都将对“伊斯兰国”组织的生存造成有效打击。
第三,西方国家的平衡和分化政策是造成中东地区分裂的重要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英法两个大国之间达成《赛克斯-皮科协定》,划定各自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构成此后中东地区分裂版图的原型。不仅如此,西方因素也贯穿了中东地区分裂进程的每一个阶段,并使得该地区的分裂态势不断加深。②
冷战结束后,以海湾战争为分水岭,中东地区逐步形成了由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为实现对中东地区的掌控,美国将该地区的力量划分为两类,一是亲美温和力量,包括海湾国家、约旦、摩洛哥、突尼斯、埃及以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等;二是反美“激进”力量,包括伊朗、利比亚、叙利亚、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这种划分意在鼓励和支持亲美温和力量对抗反美“激进”力量,不仅加剧了地区国家间的对抗,而且加剧了地区分裂的态势。中东地区国家之所以难以在反恐等重大地区问题上保持协调,很大程度上与美国人为制造的矛盾和利益分歧密切相关。
三、外部和地区大国的消极反恐政策与“越反越恐”现象
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开启了全球性反恐运动。然而15年来,国际恐怖主义非但没有被根除,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阿富汗塔利班势力历经多年围剿,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伊拉克的“基地”组织分支最终发展壮大,演变为席卷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广大地区的“伊斯兰国”组织,并且在世界各地到处煽风点火。这凸显了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越反越恐”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包括恐怖主义自身的顽固性,但同时也是外部和地区大国没有采取适应反恐形势需要的政策所致。
第一,美国等国的消极反恐政策非但不能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反而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重要原因。尽管人们无须质疑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所包含的真实反恐意图,因为“9·11”事件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安全冲击为美国的反恐战争提供了强大动力,但此后15年间,美国在中东地区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是否真正出于反恐目的,仍存在诸多疑点。换言之,美国也许抱持了一种反恐的“善意”,但它更多则是将反恐作为一种名义或者是一种次要目标,以服务于其他目标。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之一是正在寻求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萨达姆政权与“基地”组织有牵连。但直至战争结束,美国仍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萨达姆政权支持“基地”组织,也没有找到萨达姆政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真实目的意在按照美国的政治模式对伊拉克进行民主化改造,并试图以此作为其中东地区民主化改造的样板。尽管美国试图自圆其说,将民主化解读为根除恐怖主义的手段,但这反而暴露了美国在中东地区推广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意图。①事实表明,美国以反恐名义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非但没有根除恐怖主义,反而使得伊拉克成为恐怖主义势力新的策源地。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解散了伊拉克安全部队,致使伊拉克陷入了安全真空,为恐怖主义势力在该国的发展和壮大创造了条件。
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的调整可以解读为“待在必须待在的地方,能撤离时就撤离(engage where we must,disengage when wecan)”,②这一政策调整从反面表明,美国并不是真正致力于国际反恐大义的国家。如同推翻萨达姆政权并解散其安全部队造成了伊拉克安全真空一样,奥巴马撤军伊拉克也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由于秩序失控,伊拉克成为“基地”组织赖以扩大影响的另一重要战略据点。在此情况下,美国本应加大反恐力度,然而奥巴马政府非但没有投入更多的战略资源,反而在伊拉克安全部队并不具备反恐能力的情况下草率做出了从伊拉克撤军的决定,致使伊拉克安全形势每况愈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乘机坐大。
同样,当“伊斯兰国”组织于2014年初迅猛扩张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后,美国迫于压力不得不加大其在中东地区的反恐力度。美国所采取的行动固然具有反恐的一面,但其他意图也同样存在,甚至希望借助“伊斯兰国”组织力量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目标。比如,美国为“叙利亚自由军”提供的武器落入了“伊斯兰国”组织之手,美国也没有在其完全有能力的情况下摧毁“伊斯兰国”组织走私石油的通道。③在俄罗斯于2015年9月开始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后,美国和法国也加大了对中东地区军事投入的力度。就其时机选择而言,此举与其说是反恐,不如说是为了与俄罗斯争夺中东问题的话语权和地缘政治影响力。
总而言之,在2001~2015年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虽然一直高举反恐大旗,但并没有采取积极的反恐战略,而是将反恐问题作为推行中东政策的工具。美国以反恐名义发动的战争非但没有达到消灭恐怖主义的目的,反而制造了恐怖主义赖以滋生所需要的土壤。奥巴马政府“躲避”和“利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政策更为该组织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第二,外部大国的军事干预既没有达到治标的目的,也不可能完成治本的任务。诚然,军事手段在反恐方面的确取得过一些积极的成效,特别是在外部大国空中打击和当地地面武装相互配合的情况下,反恐战争能够取得势如破竹的效果。如2001年美国推翻塔利班政权,以及2015年第四季度俄罗斯和美国相继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加大力度,取得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收复失地战役的重要胜利等。这些外部军事干预确实摧毁了“伊斯兰国”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控制的基础设施,如石油走私的运输系统等,而且能够摧毁它们的有生力量。
在当前恐怖主义势力“准国家化”的背景下,外部大国的军事打击也许是一种无法回避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外部大国的军事干预是一种必然有效的解决办法。即使外部大国没有对反恐问题采取工具化的立场,真正致力于反恐战争,其军事干预的手段也无法达到消灭恐怖主义势力的目的。军事干预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国家崇尚实力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真正有效的反恐治本手段。
过于依赖外部大国军事干预解决反恐问题的错误在于将该模式在传统安全领域内的成功经验应用于非传统安全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海湾战争为标志,外部大国的军事干预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是上述军事行动涉及的是传统安全领域,其对象是特定国家的成建制军队。而如今活跃在中东地区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势力是植根于该地区脆弱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并拥有极端意识形态体系的恐怖组织,外部大国的军事干预即使能够部分摧毁其有形力量,也断然难以破坏其组织机制和网络,①因为军事打击无法根除无形的且基于特定经济基础的思想意识。
美国虽然在2001年摧毁了为“基地”组织提供庇护的塔利班政权及其基础设施,但并没有消灭恐怖主义,反而使得阿富汗成为向中东以及其他地区源源不断输送恐怖主义力量和意识形态的策源地之一。2003年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在伊拉克所实施的军事行动有反恐的一面,但终究也未能剿灭恐怖主义势力。同样,即使美国等外部大国能够摧毁“伊斯兰国”组织的部分有生力量以及基础设施,也断然难以从根本上防止恐怖主义滋生。
此外,外部大国的军事干预也更容易被极端主义势力解读为外部入侵,或者是西方势力对伊斯兰世界的欺辱,并成为恐怖主义势力借以招募新成员的口号。无论是对于中东本土的年轻人,还是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被边缘化的穆斯林群体来说,反对西方入侵都是极具煽动性的口号。哈佛大学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Walt)认为,“伊斯兰国”组织已经演变为一个“革命性国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外部力量推翻一个革命性的国家往往会加强强硬派的力量,助其扩大影响,起到相反的作用。①
第三,部分地区内国家的消极态度是“越反越恐”现象的另一深层根源。中东地区恐怖主义滋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地区主义的缺位。“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标志着恐怖主义势力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组织,而是已经演变为谋求控制一定规模的领土和人口,并按照其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对其进行统治的政治实体。但如前文指出,其生存依赖于一系列后勤保障和供应系统,包括武器走私系统、石油走私系统、金融系统、对外传播的互联网系统以及人员招募系统等,若能切断上述任何一个系统都将对“伊斯兰国”组织的生存造成有效打击。
重要提示:转载本站信息须注明来源:985论文网,具体权责及声明请参阅网站声明。
阅读提示:请自行判断信息的真实性及观点的正误,本站概不负责。
论文服务


 专科论文咨询
专科论文咨询
